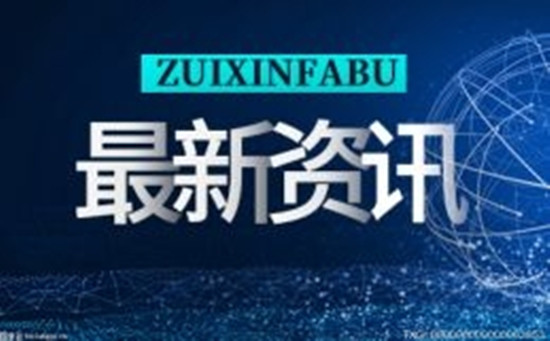BaoBao故事|外婆(随笔)
“外婆,这是什么菜?真好吃。”我嘴里嚼着青菜,歪头问。
“这个呀,叫菠菜。波儿的波,跟你名字一样。这碗里都是波儿的菜。”外婆一边说,一边跟我夹菜。
 【资料图】
【资料图】
一旁的六姨却哈哈大笑起来,说:“两个字发音一样,但菠菜的菠多一个草字头。”
外婆嘿嘿干笑道:“我以为是一个字呢。城里人说这菜吃了长个儿、聪明。波儿多吃点儿,快点长大,早点儿娶个媳妇。”说着又给我夹了一筷子。
记忆中外婆个子不是很高,但嗓门大,不论是逢年过节还是农闲,从来没见她休息过。母亲说,外婆是饿怕了,她生怕自己停歇下来,一家人就会饿肚子。
母亲的兄弟姐妹有很多,但到底有几个,她说不清楚,外婆每每听到我问起,也总是摇头叹气不说话。听母亲讲,还没解放时,家里人挺多,没有粮吃,一家大小吃过观音土,咽过米糠,还有喂猪吃的野菜。尽管想尽各种办法填肚子,但家里的人丁还是渐渐少去。
外婆连哭的力气都没有,但她还是偷偷背着家人,加入“背二哥”的行列。因为下这样的苦力,可以得到粮食或盐巴的酬劳,把这些东西带回家,至少可以让家人少挨顿饿。“背二哥”是川东特有的物资运输队,有三千年历史,主要依靠脚力,凭借双肩背篓或背架,背着粮食、盐巴、生铁或者其他生产生活物资,行走在大巴山中车辆、骡马无法通过的崎岖陡峭山路上。其劳苦艰辛的程度,从流传下来的背二歌中可见一斑,比如“背上千斤翻巴山,铁打腰杆都压弯,打双赤脚路难走,七十二道脚不干”“弯弯背架像条船,情哥背铁又背盐。鸡叫三道就起身,太阳落坡才团圆”。
这自古以来都是男人干的活儿,外婆却跟其他想法一致的女人一起,组成一支女子运输队,行走在“背二哥”的队列间。曾有诗云:“巴山谷顶白云翻,坡陡沟险走路难。妇女来当‘背二哥’,人人有双铁脚板。”
随“背二哥”队伍走了大半个月长途的外公终于回到家,不见外婆,问家里人都说不知去了哪里。外公放下一大包粮,叹了口气,说:“三天不见人,怕是饿死了。”正当悲伤和恐惧笼罩着一家人时,门外却传来外婆的大嗓门:“我回来了。”
外婆进屋看到坐在板凳上的外公,诧异地问:“你这么快回来了?”说着将肩上的布包往桌上一放,又看到外公那包粮,讪讪道:“没你拿回来的多,还是你能干。”外公伸手推了外婆一把,大声问:“谁叫你去的?这是男人们干的,你一个女人去做什么?”
外婆却大咧咧地说:“又不是我一个女人当‘背二哥’,我在妇女队里面走短途,大家背的都没男人多,不辛苦。”
外公流泪了,哽咽道:“这活是会累死人的,走着走着就倒地死了的‘背二哥’,我经常见到。你呀你呀……”
外婆低声道:“那我明天不去了。”谁知第二天外公前脚刚离开村口,外婆随后又上了路。
母亲回忆,几十年来,那是她唯一一次见到外公哭泣并和外婆红脸推搡,也是唯一一次听到外婆的嗓门变小。
后来六姨、幺姨又降生了。在外公外婆的悉心呵护下,母亲四姐妹和舅舅存活了下来。
土地包产到户后,外婆就没日没夜地干。一有空闲,就守在偌大的粮仓前发呆。
因为离县城近,外婆就搞起了副业,种植一些蔬菜瓜果挑上街卖。我在外婆家吃到的菠菜,就是她第一次试种的。每当整理菠菜去卖时,就听到她的大嗓门:“早晓得这菜营养好,多种点儿自己吃。”虽然我们吃到的都是边角菜,但从没见外婆往自己碗里夹,总是夹给孙辈们,也许她坚信孙辈们吃了这菜就真的能快点长大。
日子虽然好起来,但外婆的悲伤却渐渐多起来。舅舅自幼患有癫痫,虽然长得非常帅气,但却没有姑娘愿意嫁给他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,外公扩建住屋,正骑在梁上干活的舅舅,突然栽下来,摔破脑袋,没多久就走了。外婆大着嗓门哭了好几天,直到母亲说:“我有两个儿子,挑一个跟你住,将来跟你养老送终。”外婆这才收了声。后来因为爷爷奶奶反对,哥哥或我终究没有一个跟外公外婆同住。我的乳名叫小波,但外婆喜欢叫我“波儿”。我想,这个“儿”字,也许寄托着外婆对“养儿防老”的期待。
那时六姨、幺姨尚未出嫁,招婿入赘便被外婆挂在嘴边。最终,六姨叔和外公外婆住在了一起。过了几年,受南下打工潮影响,六姨叔外出务工,终因劳累加上生活习惯差异,染了重病,没多久就抛下妻儿和外公外婆而逝。两年后,深受无儿养老影响的五姨,在东躲西藏的超生途中难产,留下六个女儿去世。
经历接二连三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外婆,已进入耄耋之年。她逢人就说:“我命太硬,把年轻人剋死了。”
虽然命运弄人,但外婆一生无病。忽然有一天,她对六姨说:“生病了,陪我去城里看医生。”拎着一包药回来,外婆走进自己房间,第二天中午也不见出门。众人推门看时,发现她已僵硬在床,那包药只剩下一堆空瓶。
六姨为外婆树了碑,五六十个子孙后代的名字刻满了墓碑。那三个框起来的名字,特别显眼。
来源:中国青年报客户端
关键词: